概述模块——背景故事
氧蚀时代
【0】
(中新网综合讯) 当地时间2030年5月21日,第35届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在历经长达两周的艰难谈判后,于日内瓦黯然闭幕。与会各国代表未能就在2035年前大幅加速减排、建立全球碳交易市场及“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实施细则等关键议题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致意见。会议最终通过的联合声明被批评为“缺乏雄意的折中方案”。分析人士指出,主要经济体间在责任分担、资金与技术转移等核心问题上的深刻分歧难以弥合,是导致此次会议成果寥寥的主要原因。联合国秘书长在闭幕致辞中警告:“我们正在梦游般走向一场无人能够幸免的灾难,每一次的拖延和妥协,都是在关闭我们未来逃生的大门。”
【时间之内的往事】
那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个清明。天空蓝得像一块刚擦过的玻璃,阳光亮得刺眼。我和家人去郊外扫墓,发现山上的松树比往年茂密得多,林间空气甜得发腻。儿子跑得太快,摔了一跤,膝盖擦伤,血珠沁出来,竟在几分钟内凝成鲜红的硬痂——后来才知道,那是富氧环境下血小板活性激增的结果。
我们在墓前烧纸,打火机点燃金纸的瞬间,火焰“呼”地窜起半米高,差些燎到旁边的枯草。父亲嘟囔:“现在的火,怎么这么凶。”那时我们都没意识到,火之所以“凶”,是因为空气中的助燃剂已远超安全阈值。
下山时,我看见远处工业园区上空悬浮着巨大的惰性气体罩,像一只倒扣的玻璃碗——那是为了防止意外燃爆。当时我早已习惯这种景观,就像习惯越来越蓝的天、越来越绿的树。没有人相信——或者说愿意相信,我们最终会因此而毁灭。
-—— 百万立方计划幸存者
朱培鑫
【湛蓝的预警】
最初的征兆,悄然无声。
植物学家刘津廷蹲在学院老楼潮湿的北墙根,用手指捻着一片异常肥厚、色泽深绿得近乎发黑的苔藓。它的长势太快了,上周才清理过的墙角,如今又覆上了一层茸茸的绿毯,在北方干燥的春天里显得格格不入。
“光合作用效率高得离谱,”他对走来的同事嘟囔,“样本送去检测了,基因序列有点……奇怪,像是被什么外源片段插入了。”
同事不以为意:“好事啊,绿化指标又能超标完成了。现在这天,蓝得跟假的一样,空气好得让人发慌。”
刘津廷抬起头,望着那片澄澈得过分、几乎不带一丝杂色的苍穹。确实,空气清新甜润,但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心中掠过一丝难以名状的不安。
几年后,这种不安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科学争论。大气监测数据不会说谎:氧气浓度曲线那个持续而坚定的上扬坡度,让越来越多的气候学家和生物学家感到脊背发凉。学术期刊上开始出现谨慎的论文,讨论“全球光合作用异常增强”的潜在影响,但公众的视线被经济起伏、局部冲突和日益精美的娱乐产品所占据。即便偶尔有“森林自燃奇案”的报道,也被视为孤立的趣闻。
【无声的警报】
刘津廷的实验室成了数据的孤岛,也是风暴的前沿。他和他的小组,通过持续监测和复杂的模型推演,逐渐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惊的图景:大气氧浓度的上升并非均匀缓慢,而是呈现加速趋势,其核心驱动因子与南极冰盖融化后释放的某种古老微生物群落(后来被私下称为“潘多拉古菌”)及其引发的全球性基因水平转移有关。这种转移不仅作用于苔藓,更潜在地改变了绝大多数植物的光合作用机制,甚至可能影响部分微生物。他计算出,照此趋势,在三十年内,全球氧浓度将突破25%的临界点,届时,材料的氧化速率、火灾的风险将呈指数级增长。
“这不是福音,是缓刑判决书。”刘津廷在给他一位在《自然》期刊任职的老同学的信中写道。他倾尽心血完成了一篇综述论文,试图整合生物、气候、材料科学的数据,敲响警钟。论文经历了异常严格的审稿,最终被以“推测成分过多,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公众担忧”为由拒稿。一位审稿人甚至评论:“作者似乎低估了自然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人类社会的适应潜力。”
更大的压力接踵而至。学院领导找他“谈心”,委婉地提醒他“研究方向最好能与国家当前的绿色经济战略更紧密结合”。不久后,一家与“生命树”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环境评估机构”发布报告,宣称刘津廷的数据处理方法“存在瑕疵”,其风险预测模型“过于悲观”。网络上开始出现指责他“哗众取宠”、“阻碍发展”的言论。
刘津廷看着窗外愈发茂盛的校园植物,那种甜腻的空气此刻让他感到窒息。他目睹着世界朝着他预测的深渊滑去,却发不出有效的声音。他的警告要么被无视,要么被曲解,要么被强大的利益集团轻易碾碎。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和愤怒吞噬着他。他开始失眠,在深夜的实验室里,对着闪烁的数据屏幕,一遍遍复核自己的计算,结果一次次指向同一个可怕的终点。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但这种“正确”带来的不是成就感,而是目睹巨轮撞向冰山却无法改变航向的巨大痛苦。他不再试图说服世界,而是转向了几乎无人看好的绝望研究——尝试设计一种基因抑制剂,企图人为降低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为人类争取时间。这是一场孤独的、希望渺茫的赛跑。
【时间之内的往事(节选)】
摘自《遗忘的代价:人类世晚期认知偏差研究》
……回顾“氧灾”前夜,最令人扼腕的并非缺乏预警,而是人类认知系统在面对非线性威胁时的集体失灵。我们习惯于应对急性、可见的危机(如战争、地震),但对于这种缓慢累积、初期甚至呈现某些“积极”表象(如空气改善、绿化加速)的灾难,却表现出惊人的迟钝。
从南极冰盖中释放出来的“潘多拉古菌”及其引发的基因污染,是一个典型的“灰犀牛”事件。它体型巨大、行动缓慢,理论上早有充足时间规避,但各方利益集团有意无意地淡化风险……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本身,成了灾难的最佳助推剂。
若将“氧灾”的起点仅仅归于一种远古细菌的释放,那是对历史复杂性的严重简化。真正的灾难,早在第一个预警信号出现之前,就已埋藏在人类文明的基因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傲慢、制度化的贪婪,以及面对长远威胁时近乎本能的短视与自私。
当刘津廷们最初的论文在学术圈引发轻微波澜时,真正有力量的反应并非来自科学界内部的警醒,而是来自利益集团的迅速扑杀。跨国农业巨头“生命树(ArborVitae)”公司率先发布“研究”,宣称光合作用增强是“地球的自我疗愈”,是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天赐良机”。他们成功游说多国政府,将质疑声音标签为“反进步恐慌症”,并推动了一系列旨在“最大化利用新气候红利”的激进农业法案——砍伐原始雨林,改种经基因改造、生长速率极快的“超效氧木”,以获取碳汇指标和生物燃料原料。
与此同时,全球房地产和旅游业掀起了“氧吧经济”热潮。“纯净富氧社区”成为新的奢侈品符号,广告中充斥着“延年益寿”、“增强认知”的诱人承诺。精英阶层纷纷迁往森林覆盖率高的“绿区”,享受着虚假的繁荣,而对那些因异常火灾、金属脆化事故而流离失所的“氧灾难民”视而不见。国际气候谈判桌上,大国们仍在为百分之零点几的减排份额争吵不休,将“损失与损害”基金变成政治博弈的筹码。一位匿名外交官在泄露的邮件中写道:“反正我们的城市有惰性气体罩,烧不到我们头上。
“最致命的转折点发生在那场着名的”2040年全球生态评估报告“发布之后。报告以确凿的数据链证明,氧气浓度的加速上升与全球生态系统的非线性崩溃存在直接关联,并预测了“不可逆的燃爆临界点”。然而,报告的结论部分却在最后关头被大幅修改,加入了“需要更多研究”、“存在不确定性”等缓冲语句。背后是几个主要经济体的联合施压,理由是“避免引发社会恐慌和经济动荡”。真相被有意稀释、延迟、包装成可管理的“风险”,而非迫在眉睫的“灭绝”。
【窒息时代与“方舟”计划】
当氧气浓度突破25%,世界开始剧烈咳嗽。富氧火灾成为常态,不再是新闻。金属氧化加速,精密仪器故障频发。社会运转的齿轮生锈、卡顿。全球经济步入了一场有序的崩溃。刘津廷多年前的预言——曾被视为危言耸听——如今成了日常的现实。可惜,他已无法亲眼看到这迟来的“印证”。在三年前那次席卷北美大陆的“超级火灾”中,他所在的地下实验室因紧急供电系统金属部件脆化失效而彻底失联,这位孤独的先知与他未完成的救赎方案,一同湮灭在富氧的烈焰之下。
也正是在这绝望的浓雾中,中国“北辰”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那次意外发现,成了穿透阴霾的唯一光束。虫洞的另一端,“希望-1”行星的存在被严格保密,那是一个与地球几乎相同的星球——除了没有人类。于是一个激进且充满伦理争议的方案被确定:运送约两千名被遴选出的人,为将死的人类文明续命。
“一百万立方米,经过最优化设计,足够支持约两千人抵达新世界并建立初步定居点。”浙江大学博士徐象国在绝密会议上陈述,“这不仅是保存基因,更是保存活着的文明。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微缩模型。”
这个决定,瞬间将人类从面对共同命运的虚假团结,抛入了残酷的生存竞争。谁有资格登上这艘最后的方舟?
【时间之内的往事(节选)】
摘自《遴选:末日前的价值审判》
……“方舟计划”遴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是人类历史上最沉重、最赤裸的价值审判书。它迫使我们必须回答:何为人类文明最核心的财富?
是知识吗?是文化吗?是延续吗?是秩序吗?还是……权力与财富?
最终的标准是一个残酷的混合体:“跨学科创新能力”、“心理稳定性”、“生理健康度”、“年龄优势”以及“对建设新文明潜在贡献度的综合评估”。它力求“理性”、“公平”,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旧世界一切偏见的烙印。这2000个名额,成了映照人类最后面孔的镜子,映出的,是希望,也是深渊。
【临界点】
虫洞稳定器的嗡鸣声,像一只巨大的金属蜂群,盘踞在“北辰”基地地下五百米深处的主控大厅。徐象国站在观测窗前,窗玻璃是特制的,用以过滤可能从“门”那端溢出的、未知频谱的辐射。窗后并非实体景象,而是一片炫目的、不断扭曲重构的几何光斑——那是连接太阳系与“希望-1”的时空桥梁正在承受极限负载的视觉化表现。
“载荷模块‘百万立方号’,最终自检完成。生命维持系统峰值负载测试通过。“ AI合成音冰冷地播报着。
“氧气浓度,外部:30.7%。内部循环系统稳定在21%。”另一名工程师汇报,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个外部数字,意味着地球上的森林此刻已如同浸在无形汽油中,一场雷暴,甚至一块玻璃碎片聚焦的阳光,就足以点燃整片山峦。城市依靠着遍布街区的惰性气体喷洒系统苟延残喘,世界仿佛一个随时会爆燃的氧气瓶。
徐象国的目光越过光斑,似乎想穿透层层岩壁,望向地表。他想起了刘津廷,那位最早察觉异常的生物学家。他曾读过刘津廷那篇被拒的论文手稿,当时只觉得推论大胆,如今字句句都成了谶语。他想,如果当年世界能认真倾听这样一个微弱的声音,结局是否会不同?但这种假设本身,已是奢望。据说他后来投身于一种能抑制植物过度光合作用的基因工程研究,但在三年前一次席卷北美大陆的“超级火灾”后,便再无音讯。他是个警告者,但警告的声音在时代甜腻的歌唱中,微弱如蚊蚋。如今,这高浓度的氧气,这曾被视为“清新”的空气,成了扼杀文明的凶手。历史的讽刺,总带着绝对的物理冷酷。
“遴选名单最终确认锁定了吗?”徐象国问身边的助手,声音因长期熬夜而沙哑。
“委员会……刚刚完成最后一轮投票。增加了三名古语言学家和一名民俗音乐保护者,替换掉了原名单上的一名等离子物理学家和一名结构工程师。”助手低声回答,递过一份闪烁着加密符文的清单,“一共1896人。”
徐象国没有接。他知道那薄薄的电子板意味着什么。那不仅是两千个名字,那是人类文明在狂奔向悬崖时,从车厢里被迫抛下的绝大部分乘客中,勉强抢出的几件微小行李。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莎士比亚的戏剧、贝多芬的交响乐、爱因斯坦的方程……以及承载这些知识的、脆弱无比的碳基生命体的一个极小样本。一种巨大的悲怆感攫住了他,这感觉不同于面对物理难题,这是一种意识到整个物种命运重量压于肩头的窒息。“方舟”计划的残酷,不在于它只能拯救极少数人,而在于它迫使这少数人必须成为“文明”本身,他们的生存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与历史意义上的。
【时间之内的往事(节选)】
摘自《新文明宪章辩论实录:自然优先原则的诞生》
在“方舟”启航前的最后数周,一场关于新世界社会根本理念的激烈辩论,在遴选委员会内部爆发。争论的焦点并非技术路线,而是哲学根基:人类应当在新星球上建立怎样的文明? 以资源规划局局长赵德明为首的“务实派”主张,新文明的起步阶段必须奉行“效率优先”。他们提出详尽的“百年开发蓝图”,强调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希望-1行星的资源,快速重建工业体系,复制乃至超越地球的科技文明。“我们没有犯错的余地,”赵德明在会议上疾呼,“情感化的自然保护主义是奢侈的,更是危险的。” 另一边,以生态学家苏晴为代表的“自然派”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愿景。她指出,地球的毁灭正是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希望-1不是一个等待格式化硬盘,”苏晴的声音清晰而坚定,“它是一个拥有自身演化历史的全新生态系统。如果我们只是将旧世界的错误在新土地上重演,那么方舟的意义何在?我们保存的究竟是文明,还是文明的癌症?”她主张,新社会应建立在“自然优先”原则之上,人类作为新成员而非主宰者加入星球的生态网络,发展必须严格遵循生态承载力。双方阵营争论不休。务实派警告过度的环保约束将导致开局失利,可能让整个移民群体覆灭于一次恶劣天气或资源短缺。自然派则反驳,短视的掠夺性开发将重蹈覆辙,最终再次陷入生存危机。
辩论在最关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达到白热化。赵德明展示了模拟数据,证明若采用自然派的严格保护方案,前五十年的人口增长和科技恢复速度将降低40%。苏晴则播放了一段来自地球最后的保护区的影像资料——那是在全球富氧大火前拍摄的,画面中古老的森林静谧而充满生机,与当下地球的火海形成残酷对比。许多委员陷入沉默。就在僵持不下时,一位原本沉默的成员,社会学家刘予安,提出了一个融合性的框架:“我们或许陷入了一个非此即彼的误区。文明存续是底线,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存续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们能否确立一个基本原则:在保证人类文明基本存续的前提下,任何发展都必须以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破坏为目标?不是不发展,而是转向内求,发展低环境影响的精细科技和循环社会结构。我们将‘自然优先’设为伦理灯塔和长远目标,而非即刻僵化的教条,但所有短期决策都必须接受其审视。”
这一“有限自然优先”提案,经过长达三十小时的连续辩论和细节修订,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它成为《新文明宪章》的核心序言条款。章程规定,新定居点的任何重大开发项目,都必须进行强制性的生态影响评估,并优先选择对原生环境扰动最小的方案。人类将自己定位为星球的“谦逊管家”,而非绝对主人。这个决定,意味着“方舟”承载的不仅是人和技术,更是一份基于地球悲剧反思而产生的、试图与自然达成和解的新社会契约。
【启航】
倒计时归零。
“百万立方号”庞大的舰体开始缓缓移动,并非依靠传统的推进器,而是被虫洞自身产生的时空曲率梯度所牵引,像一片树叶滑入漩涡。观测窗外的几何光斑骤然放大,吞噬了一切视野,主控大厅被一片非自然的强光笼罩。
地面上,在少数几个知晓内情的高层观测站里,屏幕上的信号强度曲线剧烈跳动,然后,随着虫洞的稳定闭合,归于一条平滑的直线。观测站内一片寂静,只剩下仪器运转的低鸣和压抑的呼吸声。有人如释重负,有人掩面而泣,更多的人陷入无言的茫然。
世界并未因这艘承载着最后希望的飞船离去而有任何改变。风依然吹拂,只是更易点燃一切;天空依然湛蓝,只是这湛蓝如今意味着致命的富氧环境。绝大多数人类,依旧在为他们各自的生计、欲望、梦想挣扎,对刚刚发生的、决定物种命运的星际移民一无所知。社交媒体上依然充斥着琐碎的争吵和娱乐八卦,仿佛末日只是另一个遥远的传说
徐象国没有登上“方舟”。他的位置,让给了一位专精于地外生态系统适应的年轻生物学家。他的理由很简单:“桥已搭好,守桥人该留下了。”
他走出主控大厅,乘坐电梯升向地表。电梯门打开时,一股带着金属锈味和焦糊气息的“清新”空气涌了进来。他深吸一口这足以让旧时代人类羡慕、却令当下文明窒息的气体,抬头望向那片假一样纯净的、致命的蓝天。
“百万立方”带走了文明的火种,而留在地球上的人们,将继续在逐渐收紧的氧气枷锁中,演绎人类世最后篇章的辉煌与沉沦。 对于宇宙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生态调整;对于那艘驶向新世界的飞船,一切才刚刚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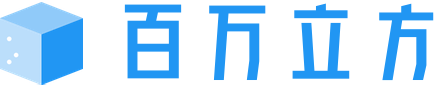
一壶开水
喵喵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