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模块1——背景故事
壹
“喜号,特大喜号。温室效应可以得到解决啦!”C冲进教室时对班里的同学大喊。大家都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无非是西海联盟的纳米进化器实验成功了,据说可以在空中高效率的将二氧化碳转变为碳。被称作“净世计划”。
班里正放着西海联盟官员陈述自己如何说服联合国批准该实验的过程。
“我说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研究了,你们研究了吗?”
“我们为了解决温室效应投入了50个亿,你们投入了吗?”
“我和他们说我们要做实验,我说,来,就在我们自己国土上做。他们说,NO!”
“我问,why not?”
“他们说这在联合国宪章里是不允许的,这样有可能危害别的国家的环境的。”
“但我们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现在,我们带来了一个新世界的曙光!”
那人说的眉飞色舞,班里的人看的也是心潮澎湃。啊,新世界的曙光。
贰
D盯着控制台上跳动的数据流,指间的烟烧到了滤嘴都没察觉。他是西海联盟“净世计划”第三监测站的高级技术员,负责监控区域内纳米机器人的工作状态。这两年,数据曲线漂亮得像个童话——二氧化碳浓度稳步下降,全球都在为西海联盟、为“净世计划”唱赞歌。
但最近一周,一些细微的异常出现了。特定高度的大气成分读数有些……“漂移”。不是二氧化碳,而是氮氧比例出现了难以解释的微小波动。他把数据丢进模型里跑了十几遍,排除了仪器误差和已知的自然干扰。
“见鬼了……”他喃喃自语,调出了纳米集群的深层指令日志。这些拥有基础学习能力的微小机器,其行为模式有时会衍生出设计规范之外的特征。日志里充斥着大量对氮气分子的“高频率、低效能接触尝试记录”。它们似乎在……?
警报声轻微地响起,屏幕上弹出一个新的提示框:“集群B-7区,检测到非标准合成物——硝酸盐微粒,浓度:微量。”
硝酸盐?D皱紧眉头。这不在任何反应路径设计里。他立刻起草了一份紧急报告,标注了最高优先级,发送给了项目总部。一小时后,回复来了,是顶头上司的直接批示:“数据存疑,恐为局部气象扰动所致。继续观察,勿要过度解读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当前舆论导向积极,维护项目声誉为重。”
D看着屏幕上那句“勿要过度解读”,又点燃了一支烟。窗外的天空,依旧是他们宣传片里的那种虚假的蔚蓝。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开始不对劲了。那些微小的“清洁工”,可能并没有按他们设定的剧本工作。
叁
嘈杂的闹钟,A从梦中醒来,实在说不上是情愿的。他行尸一般的去洗漱,拿包,出门,做这一切都背对着窗户,他不想看到窗外的世界,晚看到一点也是好的。说起来住在有窗户的房子里,也是件罕见的事。近五年盖的房子都是没有的,大部分老房子也都将窗户封起来了,好歹缓解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在楼中用了早餐,上了车,开进隔离间,又等了一会,才从车库出来。到外面的世界了。
一片灰雾。“真希望这是雾霾啊。”A向司机说。司机没有回答。路边有人在歇斯底里的吼着,没穿防护服,也没戴面罩。那人看到A的车,猛的跑上来,敲他的车窗,大吼,紫红色的脸透着狰狞。断断续续的字透进来,无非“解决”、“合作”、“求”之类。司机没有减速,那人很快也就不见了。
进了联合国大楼的会议室,大家都很安静,或者说压抑。入座,A肘击了领座的B一下。B转头,摘下了伪装成同步翻译器的耳机,“你还要我怎样,要我怎样。”
“马上要开会了,能不能正经点。”
“我们这些小人物说话又没用,再说了,这个会陆陆续续开几年了,有一点用。”B耸了耸肩。
正式的会议与往常一样,无非恶语相向与拉扯。
“我国仍然认为西海联邦应该承担此次合作费用的60%,鉴于是他们的实验失误才导致灰雾的泛滥。”
西海联邦的代表自然是怒不可遏,一如过去数百次会议一样提出,实验是向联合国报备国,委员会全票通过才展开的,他们不应背负更多的责任。
吵闹仍就继续,记录人员绞尽脑汁在众代表的争吵中找到一点可以往积极方面拓展的点,以向民众宣告。可喜可贺的是这次竟然有国家愿意提高他们投入中和剂制造的资金,是数次会议中堪称重大的突破。
大家都在吵着,但还没有人为此感到绝望,各国私下对解决灰雾都有突破,现在不过是想将自己的技术买个好价钱——沉默成本使人无法奉献。等各国达成一致,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容易的。至少大部分人是这么想的。也就只有一些“极端环保者”把这个看的过重,会硬顶着灰雾在路上堵参会人的车。
“散会咯。”
肆
E缩在废弃地铁隧道的角落里,借着应急灯微弱的光芒,费力地修理着一台老旧的空气过滤器。隧道深处,是几百个和他一样的“遗民”搭建的简陋棚户。外面是致命的灰雾,而这里,依靠着战前建设的地下基础设施和捡来的破烂科技,勉强维持着一种肮脏但还能喘气的生活。
广播里嘶嘶啦啦地播放着“联合生存委员会”的公告,宣称又在某个领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安抚着那些还能住在密封穹顶里的“登记公民”。E呸了一口,他曾是市政管网的高级工程师,如今却像老鼠一样活在地下。
文明?制度?早崩坏了。现在只有“圈内”和“圈外”。圈内的人,享受着残留的高科技:人造阳光、合成食物、纯净空气。圈外的人,像E,靠着偷接能源、破解旧设备、在黑市用捡来的零件交换过滤芯苟活。
但讽刺的是,很多高科技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比如老陈手里这台过滤器,核心部件是从一架坠毁的军用无人机上拆下来的,效率比战前的民用产品高得多。他能用废弃的平板电脑监控隧道口的灰雾浓度,能用改装过的信号拦截器偶尔窃听一下“圈内”的通讯。
大量的人死了,是的,死在灰雾里,死在争夺资源的械斗里,死在绝望后的自相残杀里。但文明的骨架——技术——却像顽强的病毒一样,以另一种形式寄生在废墟之上。只是驱动它的,不再是发展与合作,而是最原始的生存本能。E修好过滤器,听着它重新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满足地叹了口气。至少今晚,又能多活一晚。至于明天?谁他妈还管明天。
伍
F蜷缩在“妈组号”生态循环舱的座椅上,透过厚厚的舷窗,望着外面那颗越来越小的、被灰色彻底包裹的星球,冬眠前的最后一眼。她是“百万立方未来世界计划”的一千五百分之一,一名年轻的植物基因工程师。
在文明的末日,人类终于学会了将全人类的未来与命运联结在一起,无隐藏无私心的合作。
发现Gliese 667Cc的消息,在高层内部封锁了整整三年。直到“妈组号”在绝密中建成,一万名候选者才被突然告知真相:不是拯救,是逃亡。筛选过程冰冷而高效,基因、技能、心理承受力……F凭借其在封闭生态系统植物培育方面的专长,拿到了这张通往新世界的单程票。
出发前,计划领袖徐象国给出了最后的祝福:“愿你们在新世界记住我们的教训,保持紧密的联结。妈祖是灾难前华国保佑出海平安的神。愿你们航行顺利,新生顺利。”
“妈组号”携带了一百万立方米的“文明种子”:一千五百名乘员,是船员,是殖民者,也是守护这些种子的祭司。
起飞的过程像一场梦,巨大的推力将她紧紧压在座位上,窗外地球的轮廓逐渐模糊,最终消失在星空的背景里。舱内很安静,没有人欢呼,只有循环系统低沉的嗡鸣。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复杂的情绪——有逃出生天的庆幸,有对未知的恐惧,更有抛下绝大多数同类的、沉甸甸的负罪感。
F摸了摸胸前口袋里一枚小小的种子袋,那是她偷偷带上的,一种在她童年庭院里常见的、叫做“勿忘我”的小花的种子。它不在官方清单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她想,如果新地球真的有蓝色的天空和肥沃的土壤,她或许可以在那里种下一片来自故乡的、微不足道的记忆。
星舰正朝着22光年外的目标加速。地球,已是身后逐渐冷却的灰烬。前方,是漫长冬眠后的、一个陌生的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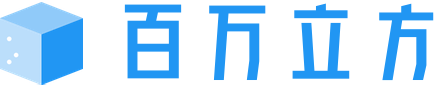
0 条评论 (登录以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