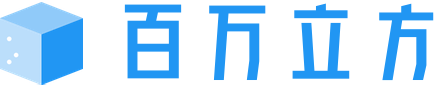概述模块2——新的挑战
一名女性“后来者”的年谱
讨论是否要接纳之后赶来的618人时,与会者一致授权调取了这些后来者简要的身份资料。这是其中一位贫穷女性的年谱。接纳这些人后,竺托邦将其称为“后来者”,以区别于1544名“先来者”,这是ai选择的非歧视性称呼。
L(姓名隐去),旧历1995年生于新疆尉犁县古勒巴格乡,维吾尔族人,有一弟,在尉犁县本地完成义务教育。
旧历2011年,16岁初中毕业,在家务农。时值新疆政府开展“靓丽工程”,L前去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学习服装裁剪、饰品制作等手艺。经月余培训,到山东一企业在当地援建的制衣厂务工,后经政府资助赴该企业在山东的总厂务工。
旧历2012-2013年,从该工厂“跳槽”,自山东辗转南下至广东、福建,在广东、福建的各处工厂务工。2013年末,在东莞稳定下来。
旧历2013-2015年,一直在东莞市郊工作、生活。这一时期,她的工资可达每月近5000元,每年寄万余元回家补贴家用、供弟弟读书。在当时的东莞,20余岁的年轻女工是当地“颇有价值”的劳动力,她们人数众多,形成了特殊的青年文化。车间之外的日子,L也逐渐加入这一群体,接触到网络和时尚文化,认识了一些同为打工者的朋友。
旧历2016年,与另一名打工者恋爱、结婚、生育一子。年末,将儿子带回尉犁县老家,托付父母抚养。
旧历2017-2021年,保持城市打工者的生活,工资时有上涨。2020年,疫情袭来,L所在工厂受到影响,订单减少,时常停工,L收入骤降。新疆的父母与弟弟时常催讨养育孩子的钱款,加之新疆政府在当地开展扶贫工程,L萌生回乡工作之念。2021年春,L回乡,丈夫继续在外打工。
旧历2021-2024年,在尉犁县的乡镇企业务工。受疫情影响,工作时断时续,且常常隔离封控,收入很不稳定,L的家庭地位因此大为下降。封控结束时,L的母亲染病,病毒与她原先的慢性病交攻,去世。
旧历2024年末,一企业与当地政府共同开展“AI+扶贫”工程,建设标注中心,招募劳动力完成数据集标注等工作,L也被吸纳其中。
旧历2024-2026年,L在标注中心工作。一开始收入较高,业务旺季可达每月一万元。但随着年轻劳动力涌入标注行业,以及半监督技术等的发展降低了数据标注业务的要求,L的收入不断减少,最低降至两千元不到,但为了照顾孩子难以抽身。2025年末,L再度怀孕,标注中心凭此理由停发工资并让L在家备孕。临近生产期、难以外出劳动时,L经广东认识的朋友指点,在线上众包平台揽收包括数据标注在内的一些零碎任务,每月收入一千余元。2026年夏生育一子。
旧历2027-2031年,继续进行标注工作,时而在尉犁周边寻找零工,但收入一直不高,还要照顾老小、操持家务,生活艰辛。依靠在外打工的丈夫汇回家的钱维持尚可的生活水平。2031年,大儿子考上衡水中学尉犁分校。
旧历2032年,世界形势渐趋紧张,经济收紧。新疆未受多大直接影响,但数据标注中心和线上众包平台都逐步关停了。L重新到附近的制造业企业务工,但找工作不比年轻时容易,收入也不高。有时兼职或打零工。这时,丈夫汇回家的钱逐渐减少。
旧历2034年,大儿子考上新疆的本科院校。丈夫停止汇款,并要求离婚。L分得一定财产,但日常收入仍不敷使用,依靠地方资助和民族资助维生。2036年,L父亲因病去世。
旧历2038年,热战争打响。各类资助钱款骤缩,工作机会减少,物价飞涨,L生活日益艰难。
旧历2042年,L来到竺托邦。
公民大会会议纪要 010216#A0001
会议基本信息
● 日期:新历公元元年2月16日
● 时间:05:00-06:30
● 地点:竺托邦议会广场
会议主题
决定是否接纳赶来的618名新人,以及在选定接纳与否的情况下如何处置。
与会人员
● 主持人:公民王普
● 与会者:竺托邦全体1544名公民
● 竺托邦中枢管理智能协助本次会议的进行。
会议内容摘要
主持人请所有人初步选择“接纳”与“不接纳”意见,初步表决。
表决结果:770:774,继续讨论。
主持人请一名持“不接纳”意见者发言。
公民尤成安:我不赞成接纳这些移民。首先,这是计划外因素,完全未经安排,其可行性未经充分论证,显而易见,会将竺托邦周密的迁移计划和建设计划完全打破。其次,主要的理由是,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民众会构成竺托邦的不安定因素。我的论据如下:这些民众普遍受教育水平低,素质较差。他们受到两种毒素的侵染,其一是贫困的乡镇地区粗鄙狡猾的风气,其二是网络环境及公共宣传中的愚民政策。第一种毒素使他们无法参与竺托邦的集体生活,时刻考虑损人利己,影响公共服务运转;第二种毒素使他们不能认同竺托邦的理念,抗拒加诸他们身上的宣传教育(假设我们接纳他们的话)。这些都只是“虚”的因素,至于“实”的因素,比如暴力和秽语的惯习、小偷小摸的习气,更不待言。何况,他们成群结队,有组织地冲击竺托邦,假设我们接纳他们,这六百人的力量一旦结党营私,会将竺托邦平衡、平等的公共权力结构完全打破,竺托邦的政治理念将毁于一旦。考虑这些因素,我们万万不能接纳这些移民。
主持人请一名持“接纳”意见者发言。
公民汪昕:我赞成接纳这些移民。我会指出上一位发言人的漏洞,他关于这些民众个体和集体的画像都不甚准确。他将这些人描述为游手好闲、拉帮结派的乡下懒汉甚或地痞无赖,但实情并非如此。主持人,我请求让管理智能调取三项数据:这些民众中随机一人的档案;他们所有人的年龄、性别、生理条件、经济状况的分布;竺托邦建设地附近路网近12小时的车流量分布。
主持人询问全体与会者是否同意授权调取数据,举手表决通过。
管理智能调取了三项数据,分发给每个与会者。
第一项数据为L的档案,除上面呈现的年谱外,还包括收入情况、家庭情况等。
第二项数据呈现在表格中:
移民人数 618
性别 男 44
女 574
年龄 0-12 80
13-60 464
60+ 74
健康程度 健康575
残疾43
曾经收入 贫穷531
中等87
第三项数据显示,近12小时内,各种私家车从竺托邦建设地周围的县市出发,向竺托邦前进,整体呈现先分散后聚拢的趋势。在开会时,仍有许多车辆在附近的公路上兜圈子,也许这些车辆搞错了竺托邦的所在地。
公民汪昕:请诸位仔细看L的年谱。我想以她为例论证:贫困地区的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诚然如此,但这并不能推导出其素质或能力的低下、或有不良习气等等。比如说,L并非始终贫困,更非思想落后闭塞。她从新疆南下打工,需要相当的勇气,她也确因打工一度致富,适应了城镇生活。她现在的贫困,固然与这片地区现在整体的贫困相关,但请诸位考察其相关性。她回来的时候,生活尚未如此窘迫,是地方产业的衰落、总体经济的下行、战争的冲击,让她和这片地区一起变穷。上一位发言人的描述,如“沾染贫困的乡镇地区粗鄙狡猾的风气”,不符合她家乡的情况,更不符合她的情况。
进一步,我想说明这些人的纳入并不会冲垮竺托邦原有的秩序。首先,上一位发言人“成群结队、有组织地冲击竺托邦”的看法显然不成立,这从车流量分布的数据就可以看出:驾驶这些车辆的人显然是独自得到信息、各自前来寻找竺托邦的,因此,车流量的分布才呈现随机和分散的样态。其次,请诸位看看这张表格:前来的民众有许多是独自携带父母或子女的女性,还有一些随家人赶来的残疾民众。这些人适合被称为“威胁”吗?
发言时长已经用完,公民汪昕向主持人请求延时,主持人准许。
公民汪昕:更准确地说,我的意思是,这些人只是当地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人口外流后留守家乡的普通民众,被父母或子女、或许还有政府的耕地和住房政策,拴在这个地方。随着经济衰退和国际形势变坏,他们生存条件日益恶化,许多人从小康或中产返贫,甚至生活难以为继。现在,他们有了一点渺茫的希望——就是我们,竺托邦。于是,他们冒险前来,只为自己和家人有万一可能活在一个更好的未来。谁说应该驱逐这些人?我们有什么伦理依据驱逐这些人?
事实上,我甚至觉得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精英主义立场。这些人所来的地区本就是被吸血的,他们作为传统所说的较低端的劳动力,是我们都知道的某些大人物眼中的耗材。现在战争打响了,我们要逃亡,要重建新世界,新世界里却仍然只有我们这些人——自然,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在战争打响前都是一般所谓城市中产技术精英,虽然无法与真正巨大的水蛭(请允许我打这个比方)相比,虽然自己相较于更高层也在供血,但相较于人数更广大的他们,我们仍然至少是半个吸血者。富国打仗,穷国买单,我们逃跑,留下他们。这种做法有违我的伦理认知,也有违——请允许我这么批评——竺托邦号称的平等主义。
主持人请一名持“不接纳”意见者发言。
公民武元槐:尽管我不支持接纳这些人,但我十分赞成上一位发言人在伦理方面的意见,我也十分同意,这些民众是可怜人,他们值得被带到新世界。然而,我还需要指出,让他们适应并参与竺托邦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鉴于上一位发言人的长篇大论,我将简短些阐释我的观点。我论证的核心是:这些人与我们之间不存在共同性,从而无法纳入竺托邦的运作。我们都属于“数字原生代”,但他们接触到网络的条件比我们差得多;我们认同民主和平等,他们则被灌输了另外的观念;我们的讨论与合作基于相似的文化背景与价值理念,他们的文化背景与价值理念则与我们相去甚远。诸如此类的差异都导致他们不可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融入竺托邦的一整套运行体系内,数月或年余的不适应足以使他们与我们产生隔阂。我们是像救助难民一样救助了他们,接下来怎么办?让他们继续当难民,或在竺托邦内当二等公民,甚至与我们隔离开来?这根本行不通,不仅有违竺托邦人人平等、尊重每个个体的基本理念,而且也不利于竺托邦的长治久安。
主持人请一名持“接纳”意见者发言。
公民王石:我支持接纳这些人。我最主要的理由恰恰与上一位发言人最主要的理由相对:我认为我们与这些人之间有相当的共同性。
仍以L的年谱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在数字技术使用方面,我们可以看到,L早在中国互联网的野蛮生长阶段,即旧历2012年,就接触到了互联网和网络文化。尽管以代际划分而论,她不属于所谓“数字原生”的一代,但她接触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时间甚至早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她也是一名所谓“数字劳工”,曾在标注中心工作,并通过众包平台承揽线上任务。尽管这不能证明她的数字技术水平,但至少说明她对数字技术的基本逻辑是熟知的。何况,诸位不要忽略旧历2020年前智能手机的普及、2025年前后一般民众可接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保障、2030年左右VR和AR技术的降价与普及,这几个事件使得一般民众能低成本地参与到数字生活中,尽管这种生活在我们看来也许是低质的,但这足以表明这些民众经过不长时间的学习后有能力嵌入到竺托邦的数字管理与服务逻辑中,盖因这种逻辑对他们本不是完全陌生的。
在政治观点、文化背景与价值理念方面,我承认,我们的观念高度一致,而他们则或多或少被“面包和马戏团”的把戏磨钝了神经。然而,他们为了一个捕风捉影的消息,冒险跑到竺托邦来,这本就是一个筛选,说明他们不是盲信者,在重要的事件上有足够的敏锐、有独立思想的能力。再谈文化,我们的顾虑无非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自贫困地区,是“乡土”的,与竺托邦整体的风格格格不入,等等。但是,在L的年表中可以鲜明地看到她的城市经验,何况乡村振兴这么多年的实践毕竟在磨平城乡差距上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何况,想象一个数字技术的熟练使用者是信息闭塞者,这也是荒谬的。我们之间最大的差异也许来自审美,毕竟他们中许多人可能习惯于抖音之流的奶头乐。但这恐怕不是关键性问题,或许我们的中产文化优越感比他们的三俗爱好还糟糕,这并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最后谈一谈最重要的民主、平等问题,这里我的看法是鲜明的:他们的基本共识应当与我们一致,道理很简单,对这两个词的追求大概刻在人的天性中。并且他们都曾见过民主和平等,哪怕是其表象。一本政治讽刺小说——原谅我记不清引文和出处——有大意如此的句子,讲的是见过这些概念的人就再也忘不掉它。去教导这些理念我甚至觉得是不必要的,而若接纳他们,要协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如前所述,我认为这里没有根本的隔阂,充其量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了佐证我的观点,我想再调取三四份档案,让诸位看看它们是否都符合我说的共性。
主持人询问全体与会者是否同意授权调取数据,举手表决通过。管理智能调取了四份档案,分发给每个与会者。
与会者都阅读完档案后,公民王石建议,由于时间紧迫,现在可以进行第二轮表决了。主持人询问与会者是否认为可以表决,与会者一致同意。
主持人请所有公民表决。
表决结果:1420:134
主持人请众人讨论接纳这些后来者的处置方案。
讨论进行了四轮,详细讨论内容略去,最终形成的处置方案已经记录在“行动项”模块中。
行动项
近期和中期事项
● 由于时间紧急,后来者闯入较为突然,初步采用的应急措施为通过安保力量将后来者集中并进行了初步交涉和安置。由于后来者以个体为单位,尚未形成任何组织架构,因此以集体性安抚为主,尚未进行一对一谈话并了解后来者诉求。安置手段:采用模块化建筑紧急搭建了类似宿舍/大通铺的房间结构,增加盥洗室数量,同时提供足量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首先保证所有后来者的基本生理需求。
● 经讨论,竺托邦决定首先对全体后来者进行一对一谈话并深入了解后来者的诉求,家庭、经济、文化教育背景及心理状态等,此后将诉求上传存档。对全体后来者进行体检并初步评估其身心健康状况。将后来者集中并向其宣传竺托邦的基本理念和生活方式,许诺竺托邦能提供的服务及公民能掌握的基本权利,强调公民需要履行的基本义务。
● 为了保证后来者快速融入新环境,保证后来者的身心健康,暂时继续采用小型宿舍的形式安置后来者,同时加快独居房间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在后来者适应环境后可以享受到和先来者相同的生活环境,彰显平等性,消弭后来者和先来者之间的隔阂。
● 为后来者设定一个至少为21天的适应期。期间将采用先来者和AI共同传授新世界理念及新生活方式科普结合的类似学校教学的手段,让后来者在逐步适应和接纳理念的过程中慢慢接受和习惯新世界的运行,并发自内心地认可和赞同竺托邦的理念。教学内容包括智能设备的使用,日常出行方式的改变,生活必需品的取用方式等等。教学的进度将根据各人接受新信息和新事物的程度而改变,同时保证每周每人至少接受一次以上的专业心理咨询,保证后来者的心理健康,帮助其适应新环境,缓解不安。每天邀请3-5名不同职业的竺托邦先来者和后来者进行友好交流(可以从背景相似的人开始),帮助双方相互了解和接纳。留出较大的空间作为临时食堂,在此所有外来者可以自由交涉,保证其自由沟通的权利。该空间内将配有少量娱乐设施。出于对后来者的安全考虑,不建议后来者离开宿舍-食堂-娱乐区的临时区域(适应区)。
● 适应期后,经过心理咨询师专业评估,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可以融入新生活的后来者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岗位并分配到和先来者相同的住所及其他相应资源。在正式进入新生活的前3天,后来者可以不进行工作(假日),也可以直接开始融入工作。在正式进入新生活的前14天,后来者需要按照和先来者相同的要求积极参与工作,在此期间如有任何不适应的生理或心理现象,可以申请返回适应区;在此期间如有违反竺托邦基本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会被遣返适应区并受到比正常公民较低一级的处罚。14天过后,后来者视为竺托邦正式公民。
● 在包括适应期在内的任何时期内,后来者和先来者都应被视为平等的,任何公民都不可以歧视或侮辱任何一方。
长期事项
● 社会化适应:我们意识到,公民在竺托邦的生活高度依赖于三个方面:信息技术、民主意识与专业技能。信息技术允许公民充分利用竺托邦内的基本设施,并且在线上平台开始新的生活;民主意识允许公民以主人的身份栖息在竺托邦内,每分每秒都在决定并建设着竺托邦的未来的感触将带给他们更多的自信心、满足感与奋斗动力;专业技能与民主意识一起,帮助公民在竺托邦找到生命的目的。除了基本的适应期之外,接下来一年内将另行增加主要面对新成员的三次小型公民会议与一次大型公民会议,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竺托邦的世界组成,并提出决定性发展意见。
● 公民角色形成:大体将公民的社会角色分为类:政治角色,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政治角色指公民通过参与竺托邦的治理而产生的权利与权力衍生的角色,自新成员开始在线上社区评议并参与两次全体大会后就认为已经形成;工作角色指公民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通过劳动产生价值所对应的社会角色;生活角色指公民自发与其他公民或组织产生联系,通过这个联系对社会其他部分产生影响所产生的角色。本部分工作中心在于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的形成:从适应期开始,我们便鼓励公民“自由地思考”,审视自身兴趣与追求,并且据此借助AI技术进行专业技术的掌握、工作的初识与体验,并最终确定工作,完成工作角色的形成。除此之外,对于老龄人口、残障人士,我们鼓励他们进行育婴、教育与后勤管理之类的工作。同时,对新成员来说,他们需要的更多是适应的时间,加之竺托邦并不会干预私人关系的形成,在竺托邦主人的归属感、产生社会价值的成就感与满足感的加持下,我们相信他们会很快形成温暖的人际关系,形成生活角色,并且完成社会角色的形成。
● 公民目标建立:新成员的到来给予我们对竺托邦世界新的思考:
● 探外资源获取:新增的人口带来了额外的能源及资源消耗,虽然短时间内,我们世界内部的核电可以满足能源上的需求,但长期来讲,核能虽然有极高的能量密度,其使用仍是有限度的,为了能源长久稳定供给,我们额外建设清洁能源获取设施的工程;另外,更多生活用品及重工业制品的需求会使得资源的消耗量激增,纵使世界内部已经建立起完善的资源回收再利用体系,更加紧张的资源周转和回收中无可避免的损耗都给资源供给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需要加紧对世界外部的探索,来获取额外的资源去做进一步的建设。
一名女性“后来者”的口述史
在第一年“旧地球日”的纪念活动策划中,有人提议为来到竺托邦的公民制作口述史档案,保存每个人的记忆。这一活动得到了一致支持。以下为L档案中的原始录音资料节录。
……那三年过后,网上的声音是抓得越来越严了,大家都能感到,不让你见到的,你就见不到。但是,口子毕竟是锁不死的。我在南方干了十来年,(东莞)这里有什么大事小事,消息总得漏点出来,然后照例是辟谣。过一阵子,嘿,谣言却能说中个五成,辟谣的事情倒是不提了。
……打仗要戒严,网上当然也得严管。不知怎么,我却听说,罗布泊这里要造艘飞船!当然马上就辟谣了,还配了照片。可是这消息邪乎,一般的谣言,辟谣了就完了,是真是假,不久就知道。这消息,不信的人是不信,信的人是坚信,想着法儿,见缝插针地传。我觉得不对劲,想,这里头有点门道。
这事时不时听人讲一出,渐渐我也有点信上了。打仗的日子多难熬,爸妈也走了,老公也跑了,这日子怎么挨过去呢?得有点盼头,即使明知是假的。我就痴想:万一有艘飞船,我和儿子一起上去……我大儿子可是不信,伙着他媳妇笑我,说我脑子坏了。这么过了两个月,突然到处在传:要起飞了!就在明天凌晨!当然,网上动作可迅速了,删帖封号抓人,一条消息最多活了十分钟。我动摇了:会是真的吗?要赌一把吗?
那天晚上根本睡不着。突然想到二零年——现在得说旧历二零年——封城前夕,网上也是这样,突然冒出一条消息。有人不信,有人觉得不会怎样,有人可是信了,连夜逃了,开着家用轿车从高速公路逃啊,也就逃出去了。我想,我不是没有逃过,十六七岁,不是从新疆逃出去了吗?现在逃了,要是消息是假的,我白跑一趟,干了桩蠢事,搞不好还得被打成寻衅滋事,认罪认罚。但日子还能更糟糕吗?不能了。要是消息是真的,那——那可——
那我现在的生活,是当时想象不到的。
我打定主意:得逃。不说我怎样,我的小儿子,有这一点点的希望,我得让他看到,我得为他买一张彩票,让他见得到中奖的机会。我拉上他——他还在睡觉,满心不情愿——跨上摩托。那还是我爸当年骑的摩托,在乡下,走远路还得靠摩托。沿着县道开,然后绕到国道,往传闻中的位置一路狂奔。说来也怪,平常空荡荡的国道,那天夜里竟然时不时见到一部轿车、一辆摩托,全是往同一个方向开的。我想,这事大概是真的了。大概骑了四五个小时,快要破晓的时候,我看到一片房子,玻璃外墙,道路特干净,甚至植物都鲜嫩,不比新疆用来防风的植物灰头土脸。房子外面围了好多车、好多人,在和谁理论什么似的,吵闹得很。到了,就是这里。停摩托的时候,我全身都在发抖。
……刚来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的,想,先上船的那批人,可不知道是怎样的大人物。后来也就没那么紧张了。毕竟现在不比过去,皇帝的生活,小老百姓绝对不敢想,不然怎么说“皇帝的金锄头”呢。现在不一样了。我在那个标注中心打工,靠电脑干活,镇政府、省政府的领导,也拿电脑干活。在这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中枢的ai,过去十年,我们问什么文心一言本来也问惯了的。何况,这里早来的那批人,也没啥当领导的。
倒是来到这里后,我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二十岁。不是臭美!当初在东莞,网上什么论坛我也混过,新新老老的港片也跟着姐妹租碟看过一轮。前些天听几个小年轻扯什么“港片黄金时代”,怀旧起来,很文艺似的,那些片子我都看过七八成咧。扯远了。我是说,他们那些文化,确实搞得很精致;但假如要说我是个老古董,是乡下人,或者我一直刷抖音,所以一点都理解不了,可没有那回事。
再说民主。先来的人把我们放进来后,该做的事做完,第一件事,让我们聚在一起,开始讲这里的理念,大讲民主、平等。其实,我们不是不懂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平等。年轻的时候,女工聚集起来,找组长、经理说理,这种事我也参加过。回新疆,镇上还搞“民主下乡”,虽然到底下没下谁也弄不清楚。容我倚老卖老说几句,这两个词,谁不想要?不想要,只是因为失望,要不到,嘴上才那么说。当然,要不到,嘴上大说特说,也捞不着好处,还惹麻烦。话说回来,也有人真不想要的,不过这样的人,不会逃到这里来。
……这段话是为“旧地球日”录的,应该是很严肃的场合,我倒瞎扯了一大通闲篇。我确实该纪念这个日子,我能逃到这里,还被允许上船,文艺点说,这是个奇迹。不过,话说回来,假使现在有个女孩子在我们镇上,读了点书,像先来的那批人一样,习气不太安分,我大概也会对她好。说到底,我们先后来的两批人,并没有那么不一样。